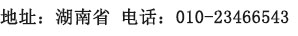母亲与济南
母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,在壬寅虎年的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,谨以此文来祭奠我的母亲。
--题记
我对济南最初的印记主要来源于我的母亲。从我记事算起,母亲曾多次和我说起她唯一一次到省会济南情景,描绘了泉城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壮美,讲到“云雾润蒸华不注,波涛声震大明湖”的趵突盛景,还讲了黑虎泉、五龙潭。让我从小就生出一种长大了要到济南看一看的愿望,后来参加高考选择院校的时,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位于济南的一所学校。
当年,母亲的济南之行既不是求学也不是旅游,而是为了找自己的舅舅借钱,归还葬父欠下的费用。
母亲的舅舅在家排行四,母亲呼其为“四舅”,是我姥姥的亲弟弟。据我的姥姥回忆,她的这位兄弟当年参加了八路军。年前后,在姥姥家中养伤近百天,和他一起的还有2名通讯员,伤愈后重新到队伍上。后来,为解决队伍给养问题,专程到我姥姥家里借钱,为帮他筹集资金,姥姥和姥爷不得已忍痛卖了30亩好地。
姥姥、姥爷视土地如骨头,卖地自然是剔骨抽筋一样的痛。
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的这位舅舅脱下戎装,转业到省会济南工作。回家探亲时,专程来看望她的姐姐和姐夫(我的姥姥和姥爷),看到外甥女(我的母亲)还未上学,便动员我的姥姥和姥爷让她上学,他再三强调,孩子是国家的财富和未来,今后国家建设需要许多有文化的人才,你们不让孩子读书是对国家财富的浪费,是对国家不负责任,如果不马上改变这种现象,他准备带外甥女到济南读书。
最终,姥姥、姥爷妥协了。
那时,母亲上学读书虽然比较晚,但是她很刻苦用功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高小毕业后就没有再继续读书,回到家里务农。但是,这一段上学的经历,为她后来成为一名执教7年的乡村教师打下了基础。
在上个世纪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母亲的父亲年龄不满50岁便因病去世,埋葬了父亲以后,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四个人,落下了近百元的欠债。一百元在那个经济极度困难的年代,对一个以务农为生,劳动力相对薄弱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。村里的许多人心里非常清楚。一些用心有别的人趁火打劫,托媒人拿着现金,来到我姥姥家里为母亲和我的大姨说媒、提亲,美其名曰“这一百块钱先用着”云云。姥姥和大姨只会无助的哭泣,母亲流着泪痛斥了这些人的丑恶嘴脸,她警告那些人“无论家里多么困难,俺娘是不会卖闺女的,块钱的帐并不多,我们有办法解决。”
在她的痛骂声中,那些所谓的媒人都灰溜溜的走了。母亲关上大门颓然的蹲在地上无声的哭了起来。
这些人并不甘心,私下里唆使赊账的人家上门催讨,其目的是给母亲和姥姥施压,迫使她们答应婚事。本家人都选择隔岸观火,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状况下,母亲和姥姥商量决定,去济南找四舅借钱还账。
此前,母亲从未出过远门,最远就是到沂水城赶大集。如今要去几百里外的济南,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济南在哪里,距离沂水有多远,一点概念都没有。后来母亲对我讲,那时只记得我姥爷曾对她说起过:从沂水去济南,大致方向是离开沂水步步西北。
那天,母亲梳了一对大辫子,白色的扎头绳,穿了一身本地布的衣裤,上身是蓝底白色小碎花图案的长褂,蓝色裤子。衣服领子、袖口、裤脚,上衣前后中缝,都沿上了长条白布,撒拉着边。左边袖子肘弯处缝着了一条白箍,右胳膊上挎一个竹提篮。
在沂水汽车站,大姨两眼哭得通红,送母亲坐上去益都(现青州市)的汽车,到了益都后如何去买票坐火车,到济南能不能找到舅舅,这一切都是未知数。
汽车到益都大概10:00,她跟着坐火车的人群一起来到火车站,看到大家都在排队买票,她也排在了队伍的后尾。正排着队,不知什么原因,前面的人“呼喇”一下子都奔向了另一个窗口,弄得她不知所措。
这时,身后想起了一阵刹车声,她转过身来,望见一辆绿色吉普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,从车上下来两位穿军装的解放军,一个是20来岁的青年,另一个是位中年人,四十上下的模样。只见这位中年军人朝她站的方向走来,她慌忙低下头,手不停地扯着衣襟。只见那人走到她的身边,停下脚步,态度和蔼的问道:“这位女学生,家是沂水的吧?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她惊异的抬起头看着这位军人答道。
“你穿的衣裳打扮已经告诉我了,这是要去哪里?”中年军人继续问。
“上济南。”他回答。
“去济南上学呀还是走亲戚?”中年军人又问。
“找俺舅。”她看着眼前的中年军人答道。
“恁舅叫什么名字?”中年军人饶有兴趣的问道。
“冯敬斋(化名)”她告诉中年军人。
“冯敬斋”中年军人把名字重复了一边,又问:“买票了吗?”
她嗫嚅着“还没有。”
只见,这位军人招呼走在前面的战士,“小马,给这位女学生捎一张到济南的票”。
买完票,中年军人和小战士把她领到候车室,告诉她火车几点到,怎么检票乘车后,才放心地离开。
看到他们走了后,她又从兜里摸出刚才买的火车票,仔细看了一遍,再次确认是“益都-济南”的,才放心的再次装进兜里。
坐在飞驰的火车上,她怀里抱着那个从老家里带来的朱红色的竹提篮,呆呆的想着心事,对面座位上的一位大嫂,好心的要帮她把提篮放置到行李架上,她害怕的拒绝了人家的好意。双手紧紧地护着提篮,就像篮子里盛着多么贵重的宝贝一样。
同车厢的一位年轻“识字班”(未出阁的女孩),好像是省歌舞团的演员,身穿当时流行的“布拉吉”,边唱歌,边跳舞,一路上歌声不断,笑声不绝,每唱完一曲,旅客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母亲当时心里想,人家心里应该是欢快的,没有一点忧愁,或者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愁。自己生在这么一个山区小村,没有兄弟,唯一的父亲又撒手人寰,自己怎么是这样一种命啊!
这时,邻座的两位妇女正在讨论,到济南下了火车后,是先去百货大楼呢,还是先去趵突泉,经过一番的商量后,她们决定先去百货大楼看看衣服、裙子什么的。此时的她,又一次摸出火车票攥在手里,偷偷地瞄一眼,是到济南的,心里彻底踏实了。听到别人讨论去哪里,心里想,自己到了济南后去哪里找县东巷8号这个地方呢?,这个地方离火车站到底有多远,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,一切都不得而知。算了不再去想了,先跟着这两位大姐到百货大楼再说。
车到济南站后,母亲当时被人流裹挟着,来到济南百货大楼。既来之则安之,她一个楼层一个楼层,一个柜台一个柜台的逛了起来。等她来到顶层,透过明亮的玻璃窗,看到太阳似乎已经西沉的时候,才猛然想起,要找的地方和人都还没有找到,自己却心安理得地逛开商店了,不免感到些许的荒唐。于是,整个人像发疯了一样,急匆匆的从三楼飞也似的跑到一楼。
出了百货大楼右转,走了不多会,看到“布政使街”的路牌,继续漫无目的的向前走了一段,穿越东西向的马路,现在来看那应该是泉城路,来到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口,因为还没有吃饭的缘故,整个人感到又累又饿,于是停下匆匆的脚步,仔细打量周边的环境。胡同内外墙上的一个路牌让她心头一喜,“县东巷”,“难道真的是这里”在心里问自己,“既然是县东巷,就到里面去找找看,说不上真的就是这里呢。”于是顾不上饿和累,遂往里面走了过去,不知不觉得来到一座大门前,门里面,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喧闹玩耍,你追我赶。她停下脚步,看到大门左侧的门垛上赫然写着“县东巷8号”的门牌号,“真的是这里,一定是父亲在天有灵,引导自己来到这里的,阿弥陀佛!”她在心里念起佛来。
看到她低着头站在大门前沉思,正在嬉戏的那群孩子也停了下来,其中一个个头稍高一点的男孩走到她的跟前问道:“干什么的?”,她答道:“找人。”接着那孩子又问:“哪里来的?”她答道:“沂水”,这时就听到这群孩子中传来“俺老家就是沂水”的话,男孩回头瞪了一眼,身后的那群孩子便不再说话,男孩又追问:“找谁呀?”,“冯敬斋”她答道。只见这个男孩听到“冯敬斋”三个字,扭头就往大院里面跑去,一边跑一边大声的喊着:“大姨,大姨,老家来人啦。”
后来,母亲对我说,当时她就像个“小朝巴”(傻子)一样,回答一个孩子的问话,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,可那时她真的就那么做的。
看来,自己要找的就是这个地方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,男孩和一位中年妇女走了出来,只见这人身形微胖,头发卷曲着,上身穿一件印花汗衫,下身穿一条月白色宽松下垂的山绸子裤子,来到跟前问道:“家是哪里?”她回答:“沂水黄山。”“哦,哪个庄?”卷发的女人又问。“胡家庄”她答道。“哎呀,是四姐家的孩子。”那个女人一边说着话,一边打量起她来了。
她诧异地看着眼前的女人,心里想,难道这就是从未见过面的妗子。
“您是妗子吗?”她轻声的问眼下这个人,那女人告诉她道:“我不是你妗子,你妗子去北京开会了,你舅舅上班去了,我是你大姨,你管我叫大姨就行啦。”原来是这样,她心里想着,不觉之间来到舅舅家的楼前。
舅舅家住一楼。那位胖大姨安排她坐下,给她端来一杯水后,便走进另一个房间,不大一会儿的功夫,从那个房间里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。“四姐家的孩子来了,你早点回来吧”,“孩子穿的很素,好像是为谁戴孝。”
后来母亲说,当时她还认为自己的舅舅在家里,故意不出来见她,说舅舅去上班是那个胖大姨欺骗她的话。然而,稍后发生的事,证明她的想法是错误的。
过了没多久,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声音由远而近,门被推开了。看到有人进来,她急忙站了起来,定睛一看,正视自己的舅舅。她怯怯地叫了一声“舅”,眼泪已似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流了下来。舅舅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,急忙走上前,拉起她的手关切的问:“是谁老了,什么时候的事?”,她告诉舅舅,一个多月前,她的父亲走完了人生的49年,抛下母亲和她姊妹三人归西而去。听说是姐夫过世了,舅舅的脸上柔和了一些,叹息了一声说道:“我让他在这里再住些日子回去,可他就是不听。唉,如果他听我的话,也不至于.....”说完话,眼眶微红,两行泪水从眼眶里流淌了出来。
她和舅舅说明来意,舅舅安慰她,不用担心钱的事情。
舅舅告诉她,家里的生活起居都由妗子一人掌管,妗子去北京开会,舅舅的手里也没有这么多的钱,不过,不用担心,他买的公债这个月到期,明天就去兑公债,实在不够再找人凑一些,嘱咐她先安心的住下来。
母亲曾对我讲,家里天天有人上门讨债,她哪有心情一个人到处玩乐。
舅舅的公债兑换了多块钱,还专门请假陪她游览大明湖、趵突泉、到省政府那边看了珍珠泉。
舅舅嘱咐她不要一个人外出,济南人多、车多、地方大,路也多,一旦转了向,恐怕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她告诉舅舅,自己一个人去过黑虎泉、五龙潭,到过大观园的时候,舅舅吃惊地看着她说:“你不怕找不到家?”,她非常自信告诉舅舅“没事,我可以坐公共汽车,也可以叫三轮车,丢不了。”听了她的话,舅舅笑着说:“你父亲到这里来,每次出去玩都是牵着我的衣裳,生怕走丢了。”“年轻人脑子好使,真的没有什么不可以!”舅舅感慨道。
在济南逗留了四天,母亲曾对我说,那时一天都不愿意在济南多待了,真想生出一对翅膀飞回胡家庄。
这是母亲年轻还在为“识字班”时到济南的一段经历,也是母亲这一生唯一一次到的最远的地方。
母亲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,一生没有享过几天福,不管生活有多艰难,她都能从容应对,以女性少有的坚韧和顽强,和我的父亲同舟共济支撑起我们这个家,这些年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各种疾病的折磨。
如今,她离开我们已经10个月15天,相信母亲已升入天堂,那里应该是一片祥和,没有病痛,也没有疾苦,再也不用打针,也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。
母亲走了,我们和母亲的母子缘分也走到了尽头,我希望用文字记录母亲的点点滴滴,搭建起一座充满魔幻的城堡,在这里母亲永远是年轻的模样,我们也永远是长不大的少年。
壹点号沂河飞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