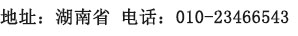下午下班开车回家,路过口泉,见马路边,数十人紧跟一个拿本子,戴眼镜的男子,和一位拿大卷尺的女子。正巧我车里拉着同事老周,他说这是口泉测量房子,估计拆迁给老住户房子呀。同车的美女小徐是八零后,她说这么破败的地方,住户也没多少了,早就该拆了。当我们提及口泉街早年的繁华,她瞠目了,嘴里嗫嚅道:“口泉街有这么热闹”?女孩年轻,当然不知道口泉街的历史。作为口泉沟的必经之路,口泉街建在了煤矿的沟口宽敞处。不远处二矿文化宫下面的山崖峭壁处,还留有民国时期骡马,驮队拉煤外运的“收费站”。旁边的庙宇香火不断,保佑着井下挖煤的矿工及其家属。当年的口泉街极尽繁华,开旅店的,卖各种生活日用品的,开饭店的,还有浴室,电影院,南来北往的客人,齐聚这里,为了生存,四处奔波。特别是民国后煤炭的大量开采,外地淘金客抓住商机,举家前来,做小本生意。口泉街生意兴隆,俨然是大同当时的商品集散地。从我记事起,还是商品社会的口泉街还十分热闹。针头线脑,胭脂水粉,笔墨纸砚,布鞋衣服,应有尽有。仿佛是北京的大栅栏。达官贵人光临,小老百姓也来。能来一次口泉街,那是无尚荣幸的事。那时候我随父母住在六矿,因交通不便,还有父亲工资低,我们少有来逛口泉街。最能听到邻居大爷说起口泉街穆桂英陂的典故,还有那里的大饭店,什么包子,烧麦,大同过油肉了,听的我们小孩子馋的的直流口水。后来父亲骑车带我和哥哥去过一次穆桂英陂,记忆中好像也没有吃过这么鲜美可口的饭菜。八十年代初期,口外姨奶奶的年轻的外孙来大同求职,住在我家。他学过木工,父亲就求人,让他跟浙江来这里做家具的一位师傅学艺。我清楚的记得他那会初中刚毕业,十五六岁的样子,一口内蒙口音。他带我坐五路车去口泉街买了一把木匠用的单面斧子,斧子锋利无比,我惊诧于口泉老街的神奇,琳琅满目的商品,二层楼的穆柯寨饭店,斗拱飞檐的民居,深不可测的小路。一路都是身穿粗布衣服的小脚老太太,还有那头戴瓜皮帽,脚蹬懒汉鞋的庄稼汉。柜台,布匹,糖果,萝卜丝。一间间店铺紧挨着,进了这家,出了那家。来一趟口泉街,就是赶了一趟大集。开了眼界,饱了口福,回家也有了吹嘘的资本。即便我没吃过油肉,谁知道?哈哈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,随着南郊区的开发,公交的通行,口泉街如垂暮老人,日渐没落。老辈人守望家园,年轻人搬到了市里的楼房。随着一家家商店的关闭,除了固定居民,老街也少有外人来。房子坍塌了,大门紧闭了,人们搬走了,这条街没有了往日的辉煌。今天,不是同事徐美女问我,我似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了。口泉老街走进了历史,而人到中年的我们,何尝不是和这条街道一样,日渐日薄西山。望着它庞大的身躯,如血管般延伸的小巷,依稀能想到它的繁荣。存在一天,就要奉献一天。让后人能够记得曾经的叫卖声,如西口互市,荡气回肠…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